做买卖要守得住底线,搞印刷的更是。
什么钱能赚什么钱不能赚,心里要有一杆秤。
行差踏错, 触碰了法律的红线,被纳入扫黄打非的范畴,得不偿失。
这是舅舅在一次酒后向我传授的箴言。

游走在灰色地带,黑白两道的钱都想吃,徘徊在治安拘留和刑事传唤的边缘,结果两头都讨不了好,点子一进去第一时间把你供出来,他坦白从宽,你留个协助组织卖淫的案底,出来后出差住个宾馆身份证都是红的,承受异样且审视的眼光,何苦呢?法网恢恢,顺藤摸瓜总有轮到你的时候,做事之前想一想。就算你自认清白,也别自我麻痹——你说你只是帮人印了点名片,可谁的名片上又会印个艳女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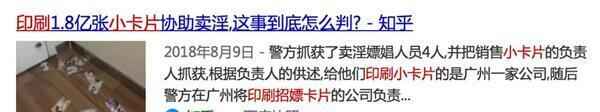
舅舅和我说过,做人要走正道,赚干净钱,吃明白饭。
他说现在凭着在作协混出来的人脉,就算帮人写匾刻碑做锦旗,一个月也能赚大几千,这还不算帮领导写报告的稿费;里子面子全都有,抽华子穿耐克,受人尊敬,妞也看着多起来了,多好?
他说,别想着怎么走歪门邪道赚第一桶金,那些发大财的都是故事,想着赚第一桶金的大多数都进去了,有些人还是无期。
都是普通老百姓,干点普通老百姓该干的事儿,别给执法机关和社会治安添堵。

他又说,可以理解,出门在外,总会有感到寂寞的时候;当一个人枯坐在逼仄的宾馆大床房里,看到门口花团锦簇的小卡片,死寂的心难免会变得活络起来。
当觉得自己无法守住底线,违法的心思蠢蠢欲动之时,要想一想后果,不要心存侥幸,去洗个冷水澡,然后打开电视看一下晚间新闻,把邪念掐灭在国际局势里。

他说,工作要分清楚边界,出差就出差,谈商务就谈商务,门缝里塞进来的商务休闲通常都是陷阱和深渊。
打电话叫过来的不是客户,名片上印的靓女九成九是老嫂子,你怀着无法将就的沮丧心情叫她回去,她还得向你索要200块打车费,否则就在你这寨子里扎下了。
“这钱,你给还是不给?”舅舅深吸了一口气:“给不给都要命。”

舅舅坦言,人在年轻时或多或少都犯过错误。
有些人将错就错,结果一错再错;有些人知错能改,浪子回头。
“人不会同时踏进一个坑,但很容易从一个坑跳进另外一个坑。”
“就像门口塞进来的十几张小卡片,上面印的人和电话都不一样,打过去全是操着XX口音的那位哥哥。”
“当你叫来了另一个,打开门你们异口同声:‘怎么还是你?’”

“人真是一种奇怪的生物。”舅舅说,他再也不试图去说服一个人,因为这个时代的人已经无法被说服了。
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,他们从只言片语和断章取义里、从自我满足的牢笼里寻求身份认同上的自洽,并以此搭建信息的藩篱。”
舅舅认为信息洪流淹没了人对“选择”两个字的理解,人的立场和价值被定向信息所塑造,而人有限的信息接收和处理能力加固了这一塑造。
“他们安守在自己的堡垒里,并对堡垒外的一切充满了攻击性。”
“我叫他别去搞,他偏要去搞,结果果然是仙人跳,人财两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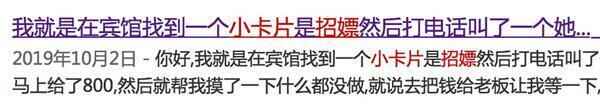
舅舅为作协的小张感到惋惜,那个意气风发,写得一手好诗的才子,现在已经淹没在滚滚人流里。
“非常不错的年轻人,就是太自满了些。”“你可以犯错,但不能一直犯错。
你上了当,就不应该再成为帮凶。”小张一身的诗才,被用在了策划卡片文案上,他从被害者变为了施害者,他幻想财务自由,却失去了人身自由。
“听说去年放出来了,有人说他在隔壁县里卖老年钙粉。”

我说,舅舅你这一通醍醐从我顶上灌下去,我一时消化不了,我得好好咀嚼一下。
舅舅从抽屉里拿出一盒东西,说外甥我一直看好你,我希望你过那些不重复错误的生活。
“你也是非常不错的年轻人。”

我说,舅舅你他妈怎么还留着这些东西,都多少年了你还是忘不了吗?舅舅说,每当自己按捺不住时,就会掏出一张卡片来仔细端详,好回忆起作为一条尚有良知的漏网之鱼所悔不当初的那些岁月。
然后把它从阳台抛向空中,看着它飘向未知的路上,自己的心境也会变得更加坚定而淡然。
“有时候,遗忘是需要记忆的,只有记起,才能忘记。”

“这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?”
“十多年吧?”
“你多久从阳台上飞一张下去,以此警醒自己?”
“一天两三张吧?”
“那你还剩这么多!”
“这是我的业。”
“我会把这个事情告诉外婆,她会弄死你!”
